傅申|张大千六十年回顾展的缘起与研究
|
站在美术史的立场来回顾整个中国绘画史,二十世纪是一个空前丰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所产生的众多画人,难以数计,张大千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同时,张大千也是伪作史上的真正高手。 近日,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田洪、蒋朝显所编的《傅申论张大千》一书,呈现了知名张大千研究专家、书画史学者傅申对张大千六十年回顾展的缘起与简介,《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特选刊这一章节。正如作者所言:“当然,张大千也不是完美的,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时,我们确实可以说他很多的画太偏于甜美,用笔流滑的应酬画太多……我是研究古画鉴别的,他的仿古、伪古,我想加以澄清,并说明其本质。这就是大千对我最有吸引力和挑战的地方。” 张大千 “血战古人”是我曾经举办的“张大千六十年回顾展”的展名,这是在借以说明张大千先生雄心万丈、勇猛精进,为向历代古人挑战,投入全部之精神。大千挟其天生异秉,又具有极强的好胜之心,他矢志要在绘画史上出一头地,花了一生的时间和心力与古人血战。 在他的前半生,他为了要能入于古人而血战;他的后半生,为了要出于古人而血战。为了要证明他是否入古,他不惜做一个制造假画的伪作者,在向古人挑战的同时,还要向那些前辈画家和鉴赏家挑战,进而向全世界的专家们挑战。在他后半生挣扎着摆脱古人的同时,还要向当代年轻一辈的画家们挑战,又要向西方的画坛挑战。最后在耄耋之年,还要跟自己衰病之躯挑战,画一幅长三十六尺、高六尺的大画,画他从未到过的庐山,耗尽心血!此画未完,他又许下心愿,要画一幅与此同大的《黄山图》。这就是一生向艺术挑战的张大千。 站在美术史的立场来回顾整个中国绘画史,我深深地觉得二十世纪是一个空前丰富的时代,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当然是中国本土的政治剧变与世界东西方文化的接触与因之产生的冲击。在这样丰富的时代所产生的众多画人,难以数计,而够得上大师、大家、名家级的画家为数亦不寡,然而在这众多画家之中,有的同道朋友为我以张大千来作研究对象,并且在美国的佛利尔美术馆为其举办回顾展感到不解,因而借此机会,作一番说明。 我想,最主要是因为我是研究绘画史的,而大千先生一生的作品,几乎就是半部中国绘画史。同时,我也是研究古画鉴别的,张大千是伪作史上第一高手,他的仿古、伪古,我想加以澄清,并说明其本质。这就是大千对我最有吸引力和挑战的地方。 一、不是锦上添花 张大千是中国画史上最爱好交朋友、最得人缘、也是最会运用人际关系和新闻媒体的画家,他将人情、世故的运用确是到了上上乘的至高境界。笔者的个性实在不喜欢做锦上添花的事。老实说,张大千的成就有目共睹,众多的吹捧揄扬文章中,本人根本不想凑热闹。笔者虽然在习画阶段(编者按:本文作者为中国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1959年毕业生,毕业前后曾获系展及省展等国画、书法多项首奖),也曾在私下学习过大千先生的山水画,但是在他生前,我没有发表过一篇揄扬或详介他的文章。当我决定要在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为他办一个展览,那也已是在他过世之后。如果他仍然在世,即使我钦服他在绘画上的成就,我也绝不会办这个展览。由此可见笔者办此一展览绝不是锦上添花,更无攀附之意。 傅申在“血战古人:张大千六十年回顾展”现场向陪同王方宇(左一)、李顺华(左二)及黄君实(右一)介绍张大千作品《文会图》 二、“血战古人:张大千六十年回顾展” 我的朋友直言问我,究竟我与大千是什么关系?大千先生生前曾否赠画给我?我是否是他的座上客?尝过大风堂的名菜?因此我想追述并分析一下我与大千先生之间的因缘。 回忆笔者在1956年考进当时中国台湾唯一的艺术系(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时,由于从小缺乏国画的教育,如同大多数的同学一样,一心一意想做一个西洋画家。但自二年级开始,不但觉得西方绘画在思想上与我很远,且连一件原画也无法看到!但随着对传统书画金石的兴趣愈来愈浓厚,于是我决定将来走中国美术的道路,要成为书画篆刻家。 在绘画上,我的兴趣是山水画,除了受到在校的黄君璧、溥心畬老师较大影响,课余又在傅狷夫老师的心香室习画。到了四年级以后,渐渐看了些张大千的画展和画册,对他描绘台湾横贯公路及阿里山、日月潭等作品有深刻印象,所以在私下他也是我取资模仿的对象之一。大学毕业前后,由同学陈瑞康兄的介绍得识书画家陈子和先生。陈先生曾对大千先生的画展出过力,其后在陈先生生活比较潦倒时,他常画一些松柏寄去巴西请大千合作以后售卖,张大千有求必应,因而使我甚为佩服其为人。我的书法和篆刻老师王壮为先生常为大千先生刻一些闲章,也得些大千先生的赠画,其中《玉照山房图》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我与大千先生第一次见面就是在王壮为老师1959年6月的50岁生日宴上,当时台北书画界名人都在,笔者是年纪最轻的小辈,属于新成立的七修金石书画社成员,与其他的社员——吴平、江兆申、沈尚贤、陈丹诚、李大木、王北岳诸兄同坐旁边一桌,故而除了被例行介绍与大千先生握手之外,并未与之交谈一言。 1964年,傅申(左)与丁翼(右)在台北拜会张大千 记得第二次见面的情形也类似,那是1964年6月19日,由叶公超、黄君璧、陈子和诸位先生联名欢宴大千先生夫妇,到场的台北艺坛人士,如马寿华、谭伯羽、陈定山、孔德成诸老,当时我正在台湾电视公司主持书法教学节目,餐后由书法家丁翼兄拉着我与大千先生合影。第二天,三人合影照片刊于报纸,并说:“与会人士百余人,其中最年轻者为青年书法家丁翼及电视节目书法教育主持人傅申,老少合影,艺坛佳话。”照片见报,只是让反对我报考艺术系的家父转变了对我的看法;但是,那一次除了合影之外,也没有交谈请益的机会。 第三次见面是在叶公超、陈雪屏二位先生推介江兆申先生与我同进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处服务之后,从那时起,我就热衷于古书画鉴别这门学问。一次,张大千先生来台北故宫博物馆观赏名画,在演讲大厅摆的凹字形的会议桌上看画,所有的贵宾及台北故宫正副院长及各处主管都一字排开,各自倚桌而坐,好像开会一样,只有书画处库房的“老牛”在旁服侍——准备一些画卷画册,但看画是由大千先生自卷自看,没有一人与他同赏或讨论。当我无意间闯进去时,就很自然地、静静地走到他背后同赏名画。记得当他看到一卷后人伪造的五代赵幹的山水卷后,说了一句俏皮话:“这一卷连照(音赵)着幹的都不是的啊!”意思是说这是一幅毫无所据的伪赵幹之作,我听了为之失笑。自此之后,也就对其他的画偶然提出一些问题,与他讨论。 张大千伪作(署名五代巨然)《溪山兰若图轴》(香港陈仁涛旧藏) 我那时正在研究五代画家巨然的传世画迹,发现了几幅是大千先生的游戏伪作,一为今存大英博物馆的传巨然《茂林叠嶂图》,一为陈仁涛氏所藏的传巨然《溪山兰若图》,另一件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五代关仝名下的《崖曲醉吟图》。这幅关仝的画,实际上是根据大千先生自藏的所谓刘道士的《湖山清晓图》伪造的。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卷巨然名下的《溪山萧寺图》卷,与《湖山清晓图》同出一手,当大千正在展卷观赏此画时,我立刻乘机请教,提出了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所谓关仝这一幅画,不应该是关仝真迹,我也想要看看他的反应如何。自我站在他肩后看画交谈起,他始终未曾回头看我,当我提出对这幅关仝画作的看法之后,他才第一次回头看了我一眼,并且说:“不会的吧,那幅绢看起来很旧的!”但我坚持说:“绢虽破旧,但画是新的!”随后他又看了一些别的古画。 张大千伪作署名五代关全《崖曲醉吟图》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 当大千先生看完了所有为他准备的画卷之后,他就起身,蒋复璁院长和其他在场同仁们到门口准备送别,大千先生一一和他们握手告别。在他离开之前,巡视全场,发现我远立一角,他就特别穿过中间,走到我的面前与我握手,并问我的“大名”,我当即答:“我叫傅申”,随后他就被拥簇着离去。 下一次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大千先生,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见到我。那是在1970年,当我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应蒋复璁院长之邀回台北故宫参加第一次中国古画讨论会,会议隆重,由蒋夫人发表开幕演说,贵宾云集,大千先生亦应邀回国,如同往常,他照例被一大堆人围绕,我只有在远处望他。当我发表有关董其昌及《画说》的作者问题的论文时,也不记得大千先生是否在座。 自从我进台北故宫博物院工作之后,因时间和精力有限,就集中精力作书画史之研究与鉴别工作,虽不至于“焚笔碎砚”,但除了写写字之外,画是几乎完全停止了。不过,我还是注意时人的画风发展,对大千先生的画展和作品也是特别留意的。 当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就读期间,方闻老师要我将沙可乐氏的藏画加以研究并整理和出版。除了藏画中有不少石涛之作,大千先生还寄存了一箱子的石涛作品,我可随时去研究、观赏。由于我对石涛真迹的大量接触,又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因此也使我对大千先生伪作石涛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 王妙莲、傅申著《鉴别研究》(StudiesinConnoisseurship,又名《沙可乐藏画研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74年 1973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鉴别研究》(StudiesinConnoisseurship),又名《沙可乐藏画研究》,书中发表了一部分大千先生伪作的石涛书画。此书出版之际,听说在大风堂的门生中,有人气愤地怂恿大千先生说:“去向法院告傅申毁谤罪。”我们知道,大千先生不但有容人之量,而且自己也常常以当众指出他当年的伪作为乐事,哪会将此事芥蒂于心呢?所以我也失去了和大千先生对簿公堂的机会。 1983年初,张大千将要过85岁的生日,《雄狮美术》发行人李贤文先生来信要我撰稿,我就以《大千与石涛》为题,罗列故事与作品,较全面地述说了石涛对他的影响,并且也不加避嫌地指出了他伪作石涛的作品。然而在稿子发出之前,即收到大千先生因病去世的消息,我非常遗憾,因为我这篇文章虽是为一般读者而写,但也有一部分内容是写给他看的。揄扬大千成就的人虽多,但是究竟有多少能真正了解他在绘画上的苦心和血战古人的过程?我自问我对他有相当程度的了解,然而他竟去世了,不能读到我的那篇文章,因此使我惘然若失! 傅申为张大千伪作(旧传宋代李公麟)《吴中三贤图卷》(原作现为美国国立佛利尔暨沙可乐美术馆收藏,本卷系复制品)题跋 1979年秋,我应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之聘,担任中国美术部主任。在该馆所藏的名画中,有一幅1957年购入的传为李公麟的《吴中三贤图》卷,经我研究,可以充分证明那是大千先生的伪作。我1985年就撰好中文稿,到1989年9月才以英文发表在香港的《ORIENTATIONS》上,该文同时指出了分散在海外各大博物馆中大千所伪作的其他唐宋古画,说明了他要借这些作品,一方面向古代名家挑战,一方面向世界上各大博物馆及国际上的中国古画专家们挑战的心理。 1987年,傅申已着手筹划““血战古人——张大千六十年回顾展”(李贤文摄引自《雄狮美术》1991年第12期页137) 佛利尔美术馆的藏品规定是不外借的,因此其也不举办借品展。1987年沙可乐东方美术馆开幕,与佛利尔美术馆合并在同一行政组下。但新馆藏品少,为弥补老馆之不足,可以举办借品展,因此我为该馆筹划了一个展览。 从我这些经历,相信读者可以看出我研究并举办大千作品展览的渊源了。我对大千先生,既没有身受其惠,也无恩可报,他也没有送过我画,虽然很想登门求证我所搜集到的流散在海外、他伪作的假画,但是知道他门客太多,不能畅谈,所以在他生前我也没有成为他的座上客,更没有尝过大风堂的美味。我钦佩他在书画上的努力、才气和成就,也很喜欢他大部分的作品,在很多方面我认为他是中国画史上难得的大家,他当然也是二十世纪最有成就的画家之一。尤其作为一个研究古书画史及鉴别工作的人来说,张大千是一个最理想的研究对象,因为他是历代画家中对传统绘画研习最深和了解最广并且是最好的画家,因此它的作品与绘画史最富有关联。在他的作品中,不但有他个人的画史,也有中国绘画的历史。 三、血战古人,画中有史 “血战古人”,我在前文已说明其蕴含的多种含义,张大千所“血战”的并不仅限于古人。张大千在绘画上所取径的方向是传统的古人和古画,与他同时代的若干大家的“西为中用”、由外向内的路径是有所不同的。大千是由内向外,从传统来开拓现代,所以他在古画中吸取养分的同时,他也一一向古人挑战。他临摹古人是为了学习,当他在仿古尤其是伪古时,显然是在与古人较量、一比高下,他绝不是要做古人的奴隶,其最终目的是超越古人,所以他在艺术的晚期力图创新,在他深厚的传统基础上,努力独开蹊径,其不甘于古人束缚的心态是极其明显的。 张大千在绘画上的范围之广、幅度之宽、功力之深、天赋之高、精进之勤、超越之速、自期之远、自负之高、成就之大,不论你喜不喜欢他,不得不承认他不但是近代大家之一。 我数年来不自觉地耗费数年的光阴在他身上,并不代表我认定了张大千是近代“唯一”、“最伟大”的画家,我喜欢并敬重的近代大家其实还不少,如大家熟知的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傅抱石、李可染、林风眠等,但是由于个人做研究的方法以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不能同时对各家都作深入的研究。不过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我在过去是研究中国传统绘画史的,而在以上的这些现代大家之中,除了黄宾虹和傅抱石差可并论之外,没有一个画家对中国绘画史像张大千那么熟悉,同时又刻意地从传世古画中加以探究和学习。诚如何怀硕兄笔下的张大千:“中国美术发达史自上古迄近代,各流派、各家法,尽集其腕底,一生作品可谓为中国画史之缩影,其为一代宗师,不但并世无匹,衡诸先人,亦罕有广博精深如大千者。”又说:“他搜罗中国绘画史上一切的精华,不论宫廷的院画或在野的文人画,不论是贵族的或民间的;不论南北、古今,他的恢宏有容、兼收并蓄,在美术史上难得如此第二人。他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大百科全书。”即使像黄宾虹这样兼有画史家素养的画家,但对古画真正能体悟其精髓的,并且在临仿学习时能做到形神俱似的,黄氏仍然远不及大千。这可以由五六十岁的黄宾虹误认张大千在20岁出头时伪仿的一幅石涛为 真迹精品,就可见出两人的高下。不过,黄氏的误鉴,倒是给大千打了一剂强心针,他从此壮了胆。 在张大千的绘画发展过程中,他不断地向一个个古代大家挑战;在他学习消化之后,就要求自己能与他们媲美,比如他最敬重八大山人,但是有一次题自己仿八大山人的得意之作说:“个山(即八大)得意处未必有此。”或自题简笔山水人物图云:“予之此幅,清湘(即石涛)能作此人物,不能为此山石;八大能作此山石,却不能为此人物,至于全幅运笔构思,起两公于九京,当亦无由落墨矣!” 等到后来,张大千不但出入宋元,上攀隋唐,他的自信心更强了。他在一幅《幽壑鸣泉图》上长题云:“欧阳公尝自称其庐山髙,今人莫能为,唯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后篇即太白亦不能为,唯杜子美能之,至于明妃曲前篇,子美亦不能为,唯吾能之。此幅宋人有其雄伟、无其温润,元人有其气韵,无其博大,明清以来毋论矣。闻斯言者,莫不莞尔而笑,愕然而惊。”大千固然有好胜雄心,但绝不是狂妄之徒,偶然发生这样的豪语,那确是他“血战古人”的成果,而不可以“狂言”视之。 当然,张大千也不是完美的,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时,我们确实可以说他很多的画太偏于甜美,用笔流滑的应酬画太多,其内容与历史、与时代、与中国的民间疾苦好像都无关而脱节,因而可以大致同意何怀硕兄对他的批评:“过于偏向唯美的营造,缺乏深厚的人性体验之表现,故他的成就,不无自外于他所处的这个苦难的时代的遗憾。”当然我们也可以反观黄宾虹、傅抱石、林风眠等人,他们的山水、花卉、仕女、高士,徐悲鸿的墨竹、麻雀等又表现了什么时代性呢?显然绘画的品评标准是多方面的,美本是艺术表现最终的一环而已。 这也是张大千个人的选择,他是有意识的,因为他明白地说:“画以表现美为主”,“真正美的东西才画,不美的就要抛弃”。绘画的优劣,不在乎唯美与否或是否有关民瘼,而在于作品本身的技巧(用笔、设色、结构)与内容的深度是否真诚和谐地配合。这与书法有某种程度的相似,就像书法的好坏并不决定于书写文字的内容,拙劣的书法并不因为写了一首有关时代苦难的诗就变成了艺术品,但是好的书法,一般都有铢两悉称的内容。 张大千入古之深是自古以来所罕见的,因而要真正了解他的作品,并不是单单能用一般的美感直觉就一目了然,因为那只是表面的了解。如果用诗来比喻,许多写景咏情的诗用白描手法,就能令读者产生共鸣;但是许多善于用典的诗,在体悟时,只用直觉的美感是不够的,还要以学识来辅助。欣赏或研究大千的画,对古画知道得愈多愈好,尤其是对大千曾经收藏过、观赏过,以及他曾经阅读过的古籍和书画著录。当然,大千创作的来源过半来自传统的古人诗文和古画,也有不少部分来自他的游历。因此,他游览过的、居住过的地方, 最好也跟随他的足迹跑一趟。身历其境,则体会又自不同。其实对于每个画家的研究都是如此,不只限于研究大千。 我对于其相关古画,由于职业关系,有某种程度的熟悉,对于大千一生创作的作品,经过多年和各方的收集,累积数千。在过去数年,我到过他的出生地内江,求学地重庆、上海,北京颐和园、苏州网师园,黄山、成都、峨眉、敦煌、兰州、香港,印度的大吉岭、阿坚塔石窟,南美洲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安地斯山温泉桥,巴西圣保罗、摩诘城八德园,美国卡迈尔的可以居、环荜庵,十七里半岛公路,东京横滨的偕乐园,欧洲的巴黎、伦敦、莱茵河,瑞士的雪山以及中国台湾的横贯公路、苏花公路、阿里山及摩耶精舍。因此,我对张大千及其绘画的了解,已经尽了我可能的范围内所有的努力了。 四、面对大千的挑战 我之研究张大千先生,除了他的画风发展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乃负有另一个绘画史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就是想要澄清流传各地的大千伪古画。游戏伪作古书画,不但是大千不讳言的事实,而且也是他的得意之事,因为除了他是在向古代名家挑战之外,也是向当时的鉴赏家、收藏家挑战。他得意,因为他是胜者。 田洪、蒋朝显编《傅申论张大千》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 我站在书画史工作者以及鉴别工作者的立场,承继同行先辈,来面对他的挑战。 就个人对美术史的认识来说,毫无疑问,我可以说他是整个中国绘画伪作史上第一人。因为其他古今的伪作家,往往只是专做一家,或至多能做数家而已,哪有像大千那样能做数十家、时代的跨度超越千余年的?他伪作之精,不但大鉴定家如黄宾虹、罗振玉、陈半丁、程霖生、叶恭绰以及他所钦佩的吴湖帆等都以他的伪作为真品,而且他伪作的历代古画分散在全世界,如中国、日本、法国、英国、瑞典和美国等各地一流博物馆里,这绝对是史无前例的一项特殊个案。在此不妨让我们套用大千的豪语,为他说出他自己不便说的话:“抑知吾之伪作古画,上自隋唐,下抵明清,足使罗振玉、黄宾虹、陈半丁、程霖生、吴湖帆等走眼,世界各大博物馆专家误鉴,五百年内外,又岂有第二人哉!” 我并不有意提高伪作及伪作家的历史地位,我之提出大千伪作这一项研究,完全是站在纯客观的绘画史研究的角度,只在求真、求事实,而无意于褒贬。 由于大千先生伪作范围之广,流传之多,当绘画史工作者研究古画时,常会遭遇到一些困难。这些流传在国内外各大博物馆里的伪作,只有在全面了解大千个人画风的发展以后,才能掌握得到。这些不同时代和不同画家的作品,如果要等待各种各样的专家去对各古画家的作品个别识破的话,可能需要集合很多人,并需要几年或几十年的时间才能作比较全面的澄清。但是如果有人能彻底地认识大千,那么由他一个人就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作全面的澄清。仅从这一角度来看,就已经非研究他不可了。 研究张大千而不研究他伪作了些什么古画,那绝对不是完整的研究和认识。他入门学习书画,虽与绝大多数的画家相同,是走临摹的路子,但是他特殊的才能,使他不论临或仿都能逼真原迹。他学古人,目标并不只限在一家、两家或明代、清代,他是不断地向古人学习和挑战,他以过关斩将的气概和姿态,由清而明,而元而宋,而唐而隋,各时代都有他的伪作。 陆抑非记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与大千的接触并录其对临摹的看法:“临摹前人的作品时,一定要不怕反复,要临到能默得出、背得熟、能以伪乱真,叫人看不出是赝品,只有这样,才能学到笔墨真谛,学到前人的神髓。”这就充分说明了他临古、仿古甚至伪古本是为学习。但是学到一种程度,他就要和古人一较长短、高下。如何与古人比较?最具体的方法之一,是看看当代的鉴赏家和博物馆专家能否将他的伪作和古画真迹区分出来,这是大千向当代专家的挑战。事实上,流传的伪作不仅是他研究和临仿古画的副产品,而且都是大千“血战古人”的精心之作。通过鉴藏家和美术史家的再三考验,他也由此建立起他的自信心。他多数的伪古画,也是临古、仿古的进一步发展,是“意与古会”的再创造,而不仅只是依样画葫芦而已。 在临、仿、伪的实践过程中,使他又有两种成就:一是使他成为眼光敏锐无比的鉴赏家,因为他观看时,能见他人之所不能见。因此,在他自叙大风堂藏画名迹时,毫不掩饰他的得意、自负之处,他说:“世尝推吾画为五百年所无,抑知吾之精鉴,足使墨林推诚,清标却步,仪周敛手,虚斋降心,五百年间,又岂有第二人哉。”一是提高自己的绘画要求和水平,他每临一次古画或伪造一古画,就会得到更深入的体会,因而就往前跃进一次。 当他潜心于某一古人的阶段,在他作伪的同时,他自己的一般创作,也往往与该一古人的风格相近。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要研究他画风的形成、成熟和改变,都与他同一时期临古、伪古的作品有某种程度上的关联。同样,当我们发现了一件大千所作的伪古画,要断定伪作的年代,就一定要依据大千画风的发展。 仅就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的立场,想要在难以数计的古画中将大千的伪作加以区别,如果只是片面地了解大千的绘画,不但困难重重,更会因误判而徒增困扰。因而,为了正确地了解大千的伪古画,就无可避免地要对他的收藏和收藏史、也包括他见过的古画甚至影印本或照片等进行全面查考。总之,这些都是有机地关联在一起,抽离而作单项的研究就会失去其意义。 综合起来说,我们要研究张大千的绘画发展,是一定需要同时了解他的收藏、鉴别、临古、仿古、伪古、游历,以及他的绘画理论和美学思想种种,否则就不够全面。比较起来,像他这样复杂博大的画家是少有的,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更多时间去研究他。个人之所以勇于接受这项挑战,一是时间上有了距离,比较客观;二是目前资讯发达,资料掌握较易;三是个人多年来对大千先生的综合研究,略有心得,以此求正于读者诸君。 (本文原文《血战古人的张大千——张大千六十年回顾展缘起与简介》载于台湾地区《雄狮美术》,选自田洪、蒋朝显编《傅申论张大千》一书(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第十三节-张大千研究缘起”,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www.9ibox.cn http://www.9ibox.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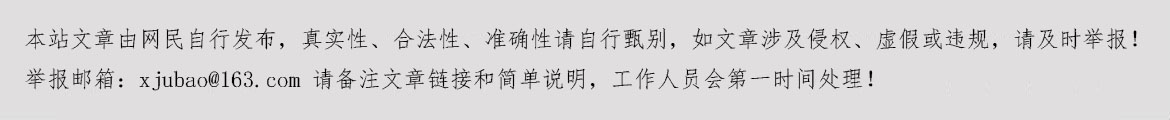
|
 鲜花 |
 握手 |
 雷人 |
 路过 |
 鸡蛋 |


